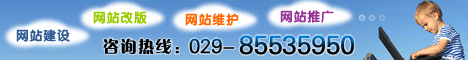[ “話語的極端民主化的確有問題,但我們不應當因此就去壓制和封閉公共討論,而是要把它變得強健、活潑和理性,也就是說提高公共討論的品質。建立好的商談體制需要制定規則” ]
“我”與“我們”的分離
第一財經日報: 你在《中國有多特殊》的《自由主義及其不滿》中寫道,1980年潘曉掀起人生意義與目標的探討,同時也說,人生意義在1990年代后就開始慢慢成為私人的事情。改革開放以后,中國社會其實經歷了一個“個體化”的過程,在這個過程中,人生目標與志向的確立似乎越來越強調“個性化”?
劉擎:新中國誕生以來的官方意識形態,是一個全面的學說——不光解釋對社會、歷史、政治和經濟,也解決道德和人生。這個在西方哲學家那里叫做“整全性的觀點”,它既是歷史觀、政治觀和社會觀,又是人生觀和道德觀。這套意識形態在“文革”結束之后遇到了問題,人們開始反思過去的歷史經驗,也開始質疑意識形態本身。當時,潘曉提出關于人生意義的討論,引起了熱烈的回應。這是我們那代人大概都知道的事情。
我想,這場討論背后都仍然有個預設:人生的意義問題是大家一起來討論,然后來解決的,好像社會可以給出一個總體性的答案。
但是人生意義問題非常復雜,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以后,每個人的生存體驗,對生活的愿景都變得越來越多樣化,你的生活理想和我的不一樣,誰都拿不出一個標準答案,因此這個問題就從公共討論中漸漸消失了。而我們所說的公共問題——制度、個人權力、社會公正等問題,成為討論的焦點。這是一個變化,表明出現了公共領域和個人領域的分化。但這種分化,在我看來也是有一些問題的。人生的意義和理想可能并不完全是一個私人的問題。
日報:其實,“個人領域”和“公共領域”是無法截然分開的?
劉擎:我不是說它們之間沒有或不應當區別,我是說這樣簡單地分開一定是有問題的。我們本來是有一整套理論,它既回答政治問題,也回答人生道德所有的問題。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,社會出現了多樣化的格局,人們就把公共政治問題和人生理性問題分開,這有一定的道理。在西方政治自由主義的理論中,就是把“正當”問題和“善”的問題分開,這是應對價值和理想多樣化事實的一個方式。就是說,我們大家有各自不同的人生信念,但我們在共同生活的基本原則方面達成共識。正當和善是有區別的,但是在一個人的生命世界里,你自己的生活理想,總是跟如何與別人相處這個問題糾纏在一起,不可能完全分離。所以我們要考慮在什么意義上這兩者可以分離,什么意義上又會發生聯系。
日報:但私人領域的擴大會對公共領域的程序、規則有一定的沖破。怎么樣維持個人領域的權利主張和社會道德規范的界限?
劉擎:公私之分有相當積極正面的意義。首先,顯然是讓個人獲得了許多自由,給了每個人更大的自主空間。這里自由的意思是,在一定的領域內,別人不能強迫我,不要把你認為好的東西強加給另一個人。國家也不能把它的意志完全強加給個人的私人生活,不能強迫你必須相信某種宗教、聽某些歌,穿某種衣服,閱讀某些書籍,等等。每個人因此有了自己更大的自由空間,這是個巨大的成就。第二,把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劃界還有個容易被人忽視的方面,就是說,我們每個人在進入公共討論的時候,或者參與公共事務的時候,不要太多地把個人的信仰、喜好、偏見和風格帶入公共領域。
但私人領域擴張帶來的問題是什么?托克維爾在《論美國的民主》中大致有這樣一種主張:一個人如果只關心私人利益或者“消極自由”,而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,就有了危險。因為公共領域就會出現公民的缺席,變得空白。那么各種各樣專斷的力量就會乘虛而入,反過來會侵蝕自由,會導致喪失自由。也就是說,哪怕只是為了維護個人自由,人們也不能僅僅關注個人的自由。
講道理的文明
日報:剛剛提到在公共領域討論問題的規則,除了學界的學者在專門的刊物、會議進行討論之外,微博也成為很多律師、學者討論的地方,你對這樣一個場域怎么看?
劉擎:現在,有人強調它的混亂和非理性的一面,這當然是個問題。互聯網的時代有一個話語民主化的趨勢,有時會變得非常經典。兩個因素造成了這種極端民主化。一是“發表零門檻”,還有一點是“匿名人格”問題。這兩重因素可能帶來討論品質的下降,這是需要嚴肅對待的問題。但我更愿意強調微博以及“自媒體”的積極意義。我認為,在現在的條件下,微博的討論非常重要,它可以讓我們看見一些本來完全沒辦法看到的東西,讓我們聽到本來可能完全被淹沒的聲音。
我更看重互聯網的開放性。話語的極端民主化的確有問題,但我們不應當因此就去壓制和封閉公共討論,而是要把它變得強健、活潑和理性,也就是說提高公共討論的品質。建立好的商談體制需要制定規則。這個規則不一定都是外部強加給大家,相反,許多討論規范是在彼此互動中慢慢學習養成的。真正有影響的博主,他們的觀點可能不一樣,但至少在一定層面上是要講道理的。說理有多種方式,可以有激情、尖銳,也可以溫和,彬彬有禮。但是講道理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規范標準。大家慢慢地正在從吵架的過程中學習理性的對話。所以,我的看法是,第一現狀不是那么糟,第二仍然有改進的趨勢和措施。
日報:如果要將其變成公共領域的更有建設性的聲音,有什么原則需要遵守?
劉擎:現在許多人說社會道德滑坡,甚至道德淪喪。其實也不盡然,真的道德淪喪,我們就不會有道德危機感和不滿。這說明我們心里還是有道德標準的。當道德淪喪的事情發生,我們會義憤。這種恰恰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標準,表明我們的社會道德狀況與這個標準相差很遠。
在微博上也一樣,大家彼此尊重對方,求同存異,這個標準是存在的,只是我們沒有達到這個標準。那怎樣辦呢?需要規則,也需要強制性的管理。微博生態的改進是可能的,但如果你憑依的軌跡是專斷的,不太講道理的,那么也無法提升一種講道理的文明。微博文化的問題是整個公共領域的建設問題,這實際上要求公民文化的發展。